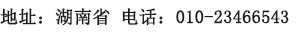庆祝建国70周年
柴达木文艺作品精选系列
马背上的“勘察队”
●三木才
1
“师兄,师傅看样子不行了。他很痛苦,治不好了,他要回家了。”
欧阳老总操着浓重的湘音给我打来了这个电话。
我有个汉族师傅,退休后回内地,现住常州。今天薄暮时分,我师傅的爱徒欧阳梦群突然来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这番话。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弄得我脑海一片空白。一时不知如何和欧阳在电话里沟通?
“师傅说给你打了几次电话,打不通。”我无言以对。手机因病毒侵袭,系统瘫痪,在客服中心重新作系统,清空了所有内存。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没有师傅和欧阳的手机号。我记性差,记不住数字,所以没记住他们的手机号码。现在陌生手机号骚扰或诈骗多,轻易不敢接。的确,一段时间显示过几次内地手机号,但确实没接。就今天这个号,要不是显示“湖南长沙”提示,我是不打算接的。匆匆地跟欧阳说了几句话,要了师傅的手机号码。
“师傅看样子不行了。”我的心跳加快了,视线也模糊了。给师傅打了电话,师傅接了电话,他声音沙哑,舌头有些硬,说话像烂醉的酒汉,吐字含混不清。他的话我完全没有听清,不知道他能否听清我的话!我糊里糊涂地挂了电话。
看来,这丙申年师傅是熬不过去了。我想到常州去看望他,但眼前有许多事情像铁链一样拴着我。讲这些理由都是空话。我去不了常州。
夜深沉而寂静。隐隐约约听到窗外的雨声,依稀有雷电的幽蓝闪光稍纵即逝。偶尔,窗外驶过车辆,车灯扫过窗户。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满脑子都是关于师傅当年的一些记忆。
人的青春岁月都有不一样的经历,对我师傅而言,是矿石造就了他的青春岁月,又是矿石将他的青春岁月打磨成了矿石的粉末。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把青春热血洒在了柴达木盆地。回眸,感知某种意境,甚感师傅那清纯与毅力、悲悯交织着我故乡的山山沟沟,交织着柴达木盆地流失的黄金岁月。我坚信时光的隧道里一定能窥见他们这一代柴达木人曾经用青春点燃的一盏盏灯火。我不怀疑这是梦,是中国梦的一束灵光。
2
我的怀念和思绪在时空中翱翔,回到了记忆落地的那个岁月里。我看见那岁月,那山峦,那人,那马。一脉时间的山峦,一个穿行在柴达木地质矿产史中的人马图景。我的马背上的“勘察队”就是这图景中的图景。
我回到了过去,回首现在的我,我呼吸的空间比古城西宁的时空还要大多了。忆往事,泪水禁不住涌出了眼眶,湿了面颊,湿了枕巾。这是醒着的梦,也是梦里的苏醒。我爬起来,走到写字台前,开了灯,坐下来抽烟,思索。
“师傅看样子不行了。”我的心被怀念、悲伤、怜悯、感恩和崇敬包围着。作为藏族,我想点燃一盏酥油灯,但又不情愿用这祈祷的方式;更怕亵渎了仍然活在人世间的地质学家的人格尊严;我想拿起笔来,记忆他人生历程中的一小段故事,但又怕驾驭不了他生平的故事情节,复原不了他的那段历史和命运。在夜的世界里,我的记忆犹如涓涓溪流,汩汩地回响,有质感和意味地滋润着属于我和师傅的一片荒野、一座大山和一汪清泉。此时此刻,我开始感动于我记忆的穿透力。我徘徊于感性和理性的岔路口,但我仍然下不了笔。我害怕写伤了一个马背上的“勘察队”;恐怕写坏了一代人的“地质精神”——柴达木精神。我下笔不易。因为我要表达的不是简单的抒情,不是诗歌小说,而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柴达木人所拥有的超凡脱俗的青春和热血的美质。是实事求是地搜索记忆中残存的柴达木人的线索,写成一篇回忆录,我深深地感到,即使我笔下生风,也写不尽“地质精神”的人格魅力。
起笔凝视白纸,感觉自己似乎无能为力,好比一个没有十分把握的外科医生手握手术刀站在了无影灯下,心里那份忐忑,别人是难以体会的。但这篇文章是非写不可,我的心这样说。
我写马背上的“勘察队”的故事还不能没有我的故事,因为马背上的“勘察队”的故事是我个人亲历。这并非喧宾夺主。在这里,我还要声明:故事里的我注定是今天的我,是一个渺小的我。
3
我们一家人曾被“阶级”久久湮没。那时,我还只是一个懵懂的毛孩,但我有“阶级恐惧综合症”。大人们的那些因“成份”而发生的纠纷和争斗,使我得了一种别人一谈”成份”就紧张,手心出汗的“病”。我默默地恐惶着,困惑和迷茫萦绕着我的童心。我在迷茫中自生,或许会幻灭。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偶然出现了一个人,一个骑着马走在西羌故土上,用地质之锤书写人生的骑士。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我原本可能小学毕业。但年冬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我们家的阶级成份划定为富牧,使我上完小学的梦破灭了。
我跟随爷爷上山放羊。二年级的我,能念《毛主席语录》,一边放羊一边给爷爷念毛主席语录。这年夏天,大队革委会主任突然到我们家,传达公社革委会的文件。说我们家没有剥削率,经审查重新划定为中牧。又降了“半格。”全家老少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欢欣鼓舞。
我在生产队当牧民,放羊、放牛、放马,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如影随形,学得一口流利的乐都方言汉语。不久,我被公社推荐到县上,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青海省卫校的老师到县上招生,招走了两男两女赤脚医生。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突然想上青海卫校了,又开始做起了上学的梦。转眼到了年,我十六岁了,即是一名共青团员,又是生产队的赤脚医生。这一年,我们家搬迁到夏窝子,我和爷爷放多只羊,50多头牛和60匹马,我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与此同时,还要背着药箱,走家串户,给生产队牧民治一些头痛脑热的小病。
4
有一天下暴雨,山洪暴发。从山谷里冲下一些红色的小石头,这种石头分量很重,砸开后石头的内部是金黄色。我爷爷非要把红石头样品送到县上“汇报”。从夏季草场到县城骑马要走整整一天的路。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手脚都不怎么灵活,但他脾气很倔犟,谁也劝不住,骑着马,皮袄怀里揣着几块红石头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从山上赶着羊、牛群牧归。刚到帐篷门口,见一个穿蓝色衣裤的陌生人从帐篷里钻出来。他笑着向我走来,和我握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大人握手。
原来爷爷从县上领着一个“勘察队”回来了。从这天起“勘察队”就住在我们家。他身材高大,走路步履轻盈,速度快,跟牧民稳健沉重的步履形成反差。我爷爷开玩笑说“,勘察队”有“小走”。比喻的是轻盈小走的骏马。他人清瘦,头发稀疏。第一次见面,我就突然联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列宁。他额头特别的突出发亮,眼窝深陷,眼神中常含笑意,嘴角上永远挂着微笑,是个特别爱问这问那的“勘察队”。不论见谁,见面就熟,马上能记住对方名字。他有个黄帆布背包,是特制的地质包。里面装着几个白色的小布袋子,袋子里是一些小石头。背包里另外还装着一把小铁锤、一个指南针、一架罗盘、卷尺、小叠刀、绘图纸、直尺、圆规、红蓝两用铅笔、放大镜、《毛主席语录》、笔记本、中华铅笔、钢笔、墨水等。胸前挂着一架“海鸥”照相机。他手里时常拿着笔记本和笔,只要和我们谈话,他就不停地记笔记。不久,我就对“勘察队”产生了好感,尤其对他的那一大堆东西产生了兴趣。我们交谈起来,他讲的汉语和我讲的汉语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在当时的语境下,我的脑子里没有“普通话”“方言”之类的概念。不知道他讲的是哪种话。但我深信我会讲汉语,识一些汉字。我们用汉语交流没有任何的困难。后来我才知道,他讲的是一种“沪普”话,而我讲的则是纯粹的“乐都汉语方言”。
5
大队革委会主任来到我家。他是来给我分配劳动任务的。说“勘察队”是根据群众提供的报矿线索来我们生产队找矿的。县上有指示,要协助他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队革委会决定派我当“勘察队”的向导和翻译,负责他的安全。生产队每天给我记十三个工分(是当时最强劳力一天的最高工分)。主任还给我和“勘察队”配备两匹武装基干民兵的战备马,让我去马群里挑选。并嘱咐我说:“给‘勘察队’挑一匹老实结实,能爬山过河的马,千万不要把人家摔坏了。”我高兴极了。当天就到马群,给“勘察队”选了一匹名叫“达根恰党”的老花马,它性情温顺,有小走,高大结实。听说是民兵连的“火夫”,而我自己则挑选了我们大队的武装基干民兵“咒食宝”(知识青年起的绰号)的战备马,名叫“仲纳黑”(黑野牛)的白蹄鬃大黑马。它有大走和狂奔两套本领,爱出“风头”,性情刚烈,勒口很僵硬。第二天,我“脱产”了。“勘察队”背着地质包;我背着药箱,我们骑着战备马上山了。我和“勘察队”都有点得意。每当路过一些牧民的帐篷时,我们策马奔跑,让那些牧羊犬狂追我们一阵。帐篷里的牧民跑出来,都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勘察队”和我。我深谙在这个年代,在牧区,时常与穿着制服或者大衣的干部骑马飞奔,无言地显示着一种政治身份和特殊荣耀。骑马飞奔时风吹到“勘察队”脸上,他那突出的光亮的额角上,稀疏而轻柔的头发飘拂起来,发丛中渗出的汗珠隐约可见。“不要跑了,慢慢走。”他说。他有点吃不消了。我们走走停停,有时下马,牵着马步行。“勘察队”人虽然瘦,但很有内劲,特别能步行。我发现他的找矿工作很“拖泥带水”,还不能一直骑在马上。他总是下马,勾着头往石头多的地方走,取出铁锤砸砸石头,拿出叠刀划划石头,用放大镜看看石头,拿笔记本记记石头,最后,从包里取出几个小布袋子,分别装些石头,然后通通装进背包。一天就这样走走停停。黄昏时,他的背包沉重起来。他的脸色有些发紫,嘴唇也结了干痂。我们跑野外,身上没有带一点口粮。每天中午的一顿饭总是到牧民的帐篷去解决。每当到牧民的帐篷,牧民对“勘察队”特别的热情,他们煮挂面、或者煮手抓,给“勘察队”亲手拌糌粑,舀奶子,酸奶。他食量小,吃不了多少就饱了。趁牧民不注意,他将几两粮票,几毛钱偷偷地塞在碗底。我用藏语提醒牧民。于是牧民从碗底取出钱和粮票,“勘察队”和牧民将“伙食费”推来推去,牧民执意不收,“勘察队”执意要牧民收。出门离开牧民帐篷后,我就对他说,你不要为难牧民,牧民会生气的,不就是吃了一顿饭吗?他认真地对我说:“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那是怎么要求的?”“那是解放军的纪律,你我又不是解放军,”我说。“我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跟你不同。”他笑眯眯地说。我也笑了。解放军人家背着自动步枪,你背着石头。我觉得他滑稽得可爱。
6
夏季的草场山清水秀,高大的山脉巍峨苍翠,这些山脉的山脊多是些湿地草场,星星点点的湿地沼泽,沼泽里的水上漂浮着地皮菜,万紫千红的野花点缀在绿色的湿地草场。“勘察队”时不时下马看野花。他问我藏语花名,我知道那朵朵黄花叫“美朵赛庆”(蒲公英),那漫山遍野的白色的花叫“毛呢”(白茅根花),但许多五颜六色的花叫不出名。他掏出了笔记本。我胡乱编花名,他胡乱做记录。见了石头滩的石头,他又下马了,他总是不肯老老实实走路。他给我说过,今天要去最高的山巅。那是一座满山乱石的悬崖峭壁,山巅没有草甸,只有青灰色、赤红色粘土和石屑的大山。但他不按照我引的路走。上了山,我才知道“勘察队”是个很任性的家伙,跟羊群里的壮山羊一样,偏偏喜欢悬崖、岩石、乱石滩、陡坡什么的。上山总是沿山脉的陡坡一侧走。有时,突然改变主意,要从山巅牵马直线下山,下到峡谷的乱石滩。我看着他有一张手绘小地图,在马背上时不时展开看,他边看地图边给我指点:从朵让沟脑往北走,五公里左右就到苏日秀麻“脑山了。咱从那里下山,到苏日哇尔麻河去看一下泉水。”我吃了一惊,他不是第一次上山吗?怎么连山山水水的名字和怎么走都一清二楚?难怪人们叫他“勘察队”。我爷爷他们几个老人还叫他“贾吉玛款”。这也没什么。为这个“向导”,生产队每天给我记十三个工分呢!再说“勘察队”下马观花,观石头,我也很喜欢看他怎么“勘察”。他从包里取出“大闹钟”一样的玩意(当时我不知道是罗盘),像猎人瞄枪一样,打开盖子,瞄我们家草场上的大山、岩层、陡坡。然后坐在地上做笔记,他取出绘图纸画岩层、画岩层台阶上的草甸,那草甸被他画成简单的几个“♂”符号。笔法很简净,我喜欢他画的画,看上去很像又很不像。他给我讲了绘图纸的功用和刻度。每到一处,一见乱石和岩石他就下马。一般情况下他牵着马,低着头,在满地的石头中寻寻觅觅,特别细心耐烦。他拣拾的石头标本全部收进他的包里,五颜六色。在我看来,是一些放牧的人在山上山下司空见惯的石头。我对他说“:你拣这些石头装在包里,背在身上,不累吗?你骑在鞍子上,鞍子骑在马背上,马背着鞍子,鞍子背着你,你背着包,包背着石头,把最下面的马累坏了。你要是早说了要这种石头,根本用不着骑马上山跑上跑下拣这些石头,石头是拣不完的。我们家帐篷旁边的河边全是这些石头,还有我爷爷给你们的那种石头。”他说:“你不懂。我不是在拣石头,我是在勘查矿脉。”我不懂。甚至没听明白。矿脉!矿脉!他这个“勘察队”如果不下马跟满地的石头打个照面,他的心似乎有一种歉意。给他当向导真无聊,走了一上午,还在帐篷附近。我时常勒住马缰绳,回头看寻找石头的“勘察队”,看到他踽踽独行。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也没去看他说的泉水。
7
“勘察队”背着一包石头,骑着马上县城去了。他不带我。说过几天就回来,去远处勘查。果然,四五天后他回来了。我们又开始上山了。这次我们上山到了最高的那座青红色的大山顶。山顶平坦,生长着红景天等植物,是一处青灰,赫红相间的秃山,山上巨石、乱石堆很多。东南面是很陡的斜坡,沟豁被河水冲涮后形成漏斗一样深的沟槽。他突然提出要牵着马下深沟。我说马下不去。于是,他就让我和马在山顶等他,他自己背着包,就像坐滑溜梯一样,用屁股往下滑,他拼死拼活滑下山沟去了。好久,谷底传来铁锤砸石头的声音。一会儿,他喊我下来。我拴好了两匹马,也滑下去了。
“重大发现。”他满脸红土尘,有一点气喘吁吁。谷底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从土层中露在外面,被“勘察队”用铁锤砸后,石头的里面是金黄色的金属。“我们把它埋好。”他说。于是,我们拣了许多大石头堆在那金色的石头上。石头堆得很高才罢休。“这事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拣了几块砸下来的标本装在背包里,然后给堆好的石头拍了照。这是他上山以来第一次拍照,他似乎舍不得拍照。他非常兴奋,竖着大拇指说:“答沙塔,沙塔(这就好了,好了)!品位很高的。”他看着我发了一阵呆,然后掏出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品位”两个字给我看。我还是不明白。“这只羊很肥。藏语怎么说?”我回答“漏错格。”“我知道’漏‘就是羊。‘朵’就是石头。朵错格。”他哈哈地笑着说。第二天,他又骑马上县城了。过了四五天又回来了。这次他带了一张黑白照片粘贴成的一幅地图。“这是秘密地图,我让你开开眼界。是飞机拍的。”他用放大镜让我看我们生产队这一块地方。用放大镜看山山水水一目了然。怪不得他早就知道我们这里的山山水水,不用问就知道地名河名。
我和“勘查队”又一次上山。这一次他说要去看苏日哇尔玛山沟的泉。一到苏日秀玛和苏日哇尔玛两条山沟的分水岭,他说:“那一面很陡,牵着马下山吧,山下的河北岸就有泉水,那泉边出松耳石”。“那一面”尚未到,他却告诉我那一面很陡。他拿出“闹钟”测量山,然后到我面前,指着我脖子上的项链,说:“没听懂吗?你的项链就是松耳石。”那时,我戴着一串由十几颗圆形松耳石串成的项链。这串项链还有一段小故事。大约在“文革”以前,有一年,我奶奶到县上逛物资交流大会,买了一串松耳石项链。买回来后,家里的、邻里的妇女们对这串项链品头论足了好一阵。这珠子太圆太光滑,颜色也太绿,颗粒也非常均匀。妇女们怀疑是假货。家里的几个姑姑谁都不要奶奶买来的这串松耳石项链。奶奶也认为自己上当买了假货,但又舍不得扔掉,就只好戴在我脖子上。后来“文革”期间,妇女们破“四旧”,把松耳石、珊瑚等珍贵首饰全都扔进河里或随便扔了。破“四旧”时,无人问津我脖子上的这串“假货”。那时,我只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小男孩,红卫兵不在乎我脖子上的这串“假”松耳石。这串项链就像我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戴着它渡过了七八个春秋。我对“勘查队”说,我的项链是假松耳石,他仔细看了看,说不是假的,是真松耳石。他说品相还不错。这下我又长见识了。汉语的“松耳石”就是藏语的“宇”。第一次听说我们这山沟里也产松耳石,我对“勘查队”的话坚信不疑。下山之后,我们到牧民帐篷吃午饭。牧民问“勘查队”有啥矿石。“勘查队”说你们这里的泉水边有松耳石。我翻译给牧民。牧民哈哈大笑,说:“他在胡说呢。连我们山里都有‘宇’,国家把‘宇’卖给我们干啥?”“泉边有一些好看的石头,真的有点像‘宇’,他当成是‘宇’了。”端饭的女主人说。
泉水边散布着一些淡绿色卵石。“勘查队”说这就是松耳石。他拣了几块大一点的装在包里。我看也不太像‘宇’。后来,他回了一趟队部,加工了那几块松耳石,带回来让牧民参观。牧民们很惊讶。
8
有一天,在山上,遇见了几个放牧的小伙。“勘察队”像查户口一样一一询问姓名、父母名,帐篷住在何处等。又一一记在笔记本上。那天天色阴暗,远处的山若隐若现。绿色的草上挂满了露珠。片刻,山恋的色调变得更暗,变成了一片氤氲,下起毛毛雨来。我和“勘察队”到一户牧民家避雨。阴雨天气,帐篷里烧的牛粪烟散不出去。帐篷里的人被烟燻着流泪,那讨厌的雨丝一个劲地往里扑,把刚往外窜的烟又压回了帐篷。“勘察队”一边擦揩眼泪,一边对我说:“你们生产队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都改了名,取了革命的名字,像刚才那些小伙,卫东、红卫、东风、红旗、忠于。你的名字不好听,为什么不起个革命名字呢?”我没有回答。当初没取革命的名字是因为成份不好,怕不配。“你改成虞峻得了。”他说。我问啥意思。他说:“你随我姓,名峻,天峻山的峻。你们藏族同胞没姓不是吗?我的姓留给你作纪念。”他笑眯眯地说,以后给我当表弟。“”他拿出笔记本,把“虞”字一笔一画地写在纸上,让我看。我用手指在地上照着写。这一个字是我当年学到的,并铭记在心的第一个最复杂的汉字。“我不想改名。”我说。“不想改就别改了。人都有自己的姓名嘛!你也别老叫我‘勘察队’了,勘察队是一个单位的名称。我叫虞叔和。以后就叫我’勘察老虞’得了。”他又把“叔和”二字写在纸上让我看。从那天起,我叫他“老虞”了。后来,跟着他来了一批地质队员,他们称呼他“虞工”或“虞师傅”。我跟着他们叫他“虞师傅”。他在地质队员面前常常夸我聪明好学。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说不上学太可惜了等等。我说有机会的话,我想上青海卫校。他们“唔唔”地应着。
9
在跟随虞师傅上山寻找矿脉的那些日子里,他教会我很多的地质矿产方面的知识。诸如鉴定矿石的硬度、质量等。一般的老百姓有可能分不清方解石和水晶石,用水晶石看白纸上的黑字,字形不会发生变化,而用透明得像水晶一样的方解石看黑字,黑字就会变成重叠字;水晶用阳光照射后的透影为彩虹光,而方解石则无彩虹光。用刀刻划,可以知道石头“表里”是否如一,可以鉴别矿石的硬度等等。我掌握了看指南针和罗盘的技巧。
在我们生产队夏季草场的大山中寻找矿脉的日子里,虞师傅骑马走遍山山沟沟,收集了许多矿石标本。他给每块矿石都编写了“个人档案”。他请教了许多牧民,记下了许多矿石的名称,他用非常工整的楷体汉字将音译的矿石藏语名称记录在笔记本上。他记忆超人,藏语矿石名称过耳不忘,而且发音很准。他还另外记录藏语日常用语,学习常用藏语单词。在较短时间内,能和牧民直接用藏语交流。我这个向导第一次无用武之地了,到后来,连当翻译的职务也受到了“冲击”。他又骑马去县城,在县城举办天峻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矿石标本展览,供全县干部职工、学生、牧民群众参观和学习。通过展览普及矿产资源知识。利用这一机会,他拜访县上的老藏医才夫旦、宗金木等人,了解和学习藏医药用矿石名称、产地等。在天峻勘查矿产资源的两年时间里,虞师傅掌握了许多药用矿石名称、产地等。他与牧民交谈,用藏语讲起藏药药用矿石名称、产地时,使藏族牧民佩服得啧啧称道,无话可说。甚至有许多药用矿石名称富有诗性,令人耳目一新。他那不畏艰辛,吃苦耐劳,乐于奉献,与山区牧民打成一片,与大山岩石融为一体的精神感动了当地的牧民,也包括我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少年;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骑马同上山的工作作风和优秀品质,赢得了广大牧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在生产队里,所有的牧民都亲切而自豪地称虞师傅为“我家勘察队”、“勘查达勋”(骑马勘查)。
10
事隔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虞师傅的地质生涯,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人格气场。把人的思想捆绑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虞师傅在大山深处将地质人的洒脱发挥到了极致,他用罗盘启动路线,用指南针指明方向,用矿锤敲打率真,用矿石书写人生。他挣脱思想的捆绑和束缚,把心思放逐到大山的怀抱里,放逐到矿石的多彩天物中,塑造了一种马背地质精神,这种精神留在了广袤的草原,留在了广大的牧民群众中!
虞师傅背着地质包,骑着马儿游历了总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的天峻县,其中包括九个公社、三十余个生产大队。他吃的是百家饭,走的是千座山。他在天峻寻找矿脉的两年里,千辛万苦,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积累起来的寻矿成果,写成了一部沉甸甸的文字报告,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天峻县人民政府、青海省地质矿产局。虞师傅在近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海西岁月—天峻牧区两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小心谨慎地依靠群众,克服困难,骑马跑完九个乡,仅遥远的苏里乡因种种原因无法前往,那里有无矿石线索成为悬念。”
一九七一年八月,我护送虞师傅和他的数十名地质队员上天峻县。那时,县城北边的布哈河没有桥。我们一行骑马涉过布哈河,到达县城时,天空乌云密布,哗啦啦下起了大雨。这场雨一下就是几天。本来我是将地质队送到县城的第二天要赶着地质队员的坐骑重返生产队的。但阴雨连绵,布哈河水势涨高,虞师傅不让我独自回去。我只好白天放马,晚上将马群赶回县城,圈在县人委马棚里,和地质队员一起吃住在县招待所。这场雨连续下了几天几夜,不料,却改变了我的命运,它成了我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命运转折点。这一年来形影不离的虞师傅,在一天晚上吃饭时,突然问我:“你上学去吧!你不是想上青海卫校吗?我给你牵好线了。”我一下子懵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怀疑听错了话。“青海卫校招生老师到天峻了,就住在招待所。我给他推荐了你。他说要让你参加考试。就考你语文和数学。等你吃完饭我带你去。”我吃饭的手开始发抖,手心出汗,就像前几年听到“阶级成份”字眼时的那种紧张袭上心来。但心情却是不一样的。
虞师傅领我去见青海卫校招生老师,招生老师随手拿一张《青海日报》让我念。我高声读起来,大部分文字都读下来了。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道算数题。是两位数的加减乘除四道题,我把加减乘三道题做下来,除法不会做。“文化程度太低。”招生老师自言自语地说。“在天峻牧区小孩子中这是最聪明的孩子。他还是一名共青团员、赤脚医生呢!今天他有些紧张,没发挥好。”虞师傅说。“行吧,上一年文化补习班。”招生老师说。招生老师又说,他要到乌兰县招生,让我在九月某日自己到青海卫校报到,抓紧办理户口和团关系等等。“他从没出过天峻,没坐过班车,他一个人去西宁不安全,家里困难,没有人送他。孟老师求你了,在乌兰招完生你回天峻来,亲自接他走。这边的手续由我给他办理,不耽误。”虞师傅说。“只能这样了,还有一张体格检查表,你陪他去检查吧!。”招生老师说。我上青海卫校的梦想就这样实现了。第二天,久雨初晴。虞师傅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自行车,他把我捎在后面,医院做体格检查。他人脉很广,每到一个科室,都有人热情地跟虞师傅打招呼,我那张体格检查表满纸“√”。九月十二日,我跟着青海卫校的招生老师,坐上了去西宁的班车。这一年,我是天峻县唯一有幸被青海卫校录取的牧区学生
11
我圆了上青海卫校的梦,但虞师傅的梦还在做。他没有了翻译和向导,自己骑着马儿在大山深谷里独往独来,偶尔,也有队员作伴。年复一年,他走在天峻的高山峻岭中,走在乌兰的大漠戈壁中,走在茫崖冷湖的雅丹迷宫中,为了柴达木的地质矿产事业,他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山山水水,在柴达木工作了近半个世纪。当年年少的我,如今是一位步入暮年的退休老干部,虞师傅年近耄耋,但他游历高山深谷,探索地质奥妙,一直活跃在地质勘查界,奔走于国内外。他虽然退休安居在内地,但只要有机会,就会返回柴达木,返回天峻。高山是他梦中的乐园,五颜六色的矿石是他心灵的保健品,山川河流、大漠雅丹是他的故乡。他在回忆文章中如是说:“怀着对天峻的眷念和报矿点的一些悬念,我在年过古稀的40年后,年重返故土,交通方便圆了我去苏里的梦。据报矿点的记忆,还顺便证实了三处矿产地。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无止境,对地质矿产的勘探和研究同样如此。在矿产业迅速发展、资源消耗快、单矿采销支撑地方经济的现今,如果尽快摸清资源家底,合理有序的探索和开发新资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将促进天峻县的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年,我正在编撰新《天峻县志》,因为矿产资源资料缺乏,无从下笔,经请示县政府,同意邀请虞师傅从内地返回天峻。帮助天峻县考察和整理县志所需矿产资源资料。这次,他带领他的徒弟欧阳梦群等五名地质专家来天峻,我陪同他们考察走访苏里乡等地区,他给县志提供了许多权威性资料,并请他亲自写了矿产资源编目。这次返回后,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对天峻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上述建议。这次陪同他考察苏里地区矿产资源,他异常兴奋,仍然和当年一样,所不同的是坐着越野车,整天山山沟沟地考察。年近八十岁的他,仍然步履轻盈,没有半点疲劳神态。他对我说:“最好的保健就是经常上山,贴近大自然。”夜晚返回苏里乡,大家累得坐不住,一个个躺在床上昏昏睡去,虞师傅却提着水桶,悄悄出门,到几百米远的苏里乡饮用泉提着一桶水回来,这件事使我无地自容。他勤劳朴素的本质,吃苦担当的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并始终激励着我,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
12
虞师傅当年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年8月,他自愿加入支援三线建设的行列,从大上海来到青海海西,从事地质和矿产事业,这一干就是三十年。他仅在天峻县骑马寻矿的两年中,向有关部门报告矿石线索13处。给天峻县交了一部完整的矿产资源分布报告,并附手绘图纸。可惜在“文革”中,这部报告丢失或销毁。他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归功于牧区群众,时时满怀感恩之心,在艰苦的岁月里,牧民群众对他的帮助铭记于心。在苏里考察的日子里,他时不时向我问起一些当年他结识的牧民的名字和现在的情况,由于这些牧民大多已经不在人世,我不想告诉他实情,他就一再追问,我只好如实相告,他在颠簸的车里哇哇大哭,同车的人都被感动,大家泪流满面。他说:“虔诚信仰佛教的藏族同胞善良、真诚。所到之处无偿为我提供线索,主动带路看矿,管好我的马,为我提供食品,如奶茶、糌粑、牛奶煮挂面,手抓羊肉、油饼、野蒜炒羊肉粉条。每次分别时都热情地叮嘱,下次一定来家里住,还拒收钱和粮票。
现在,我们这些人各方面都托了党和政府关怀,物质生活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如今人们缺少的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启蒙,在那个年代,虞师傅只是一名普通的勘察队员,他的行为就是那个时代最普通、最平凡的行为。我们也很清楚,心里明明白白,有一种精神代表了一个时代,雷锋、王杰、焦裕禄精神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这些精神从诞生的那天起,鼓舞和激励了国人。虞叔和师傅骑马寻矿,穿着破了的鞋子、衣服。但他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时代赋予这一代人的最健全的人格和生命力!
虞师傅是一位有成就的地质矿产专家。年第28届世界地质大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虞师傅的《中国青海茫崖石棉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条件》论文代表青海省入编《中国论文集》。但他从不张扬和自满。他是柴达木资深地质矿产专家,退休后被国内一些矿产企业聘请,频繁往返于中亚西亚,为国内矿产企业勘探出谋划策,但他从来不为金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是民盟常州市金坛区支部主委和学术带头人之一,但他始终低调做人,从不骄傲自满,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柴达木人共有的“精神基因”,这就是柴达木精神,是鲜活鲜活的柴达木精神。是一代又一代柴达木人在开发建设柴达木的艰苦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先进思想和优良作风,体现在个体的人身上的复合。难怪理论家称“柴达木精神”为“地质精神”!
柴达木精神的思想内涵被定义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进取,无私奉献;不断开拓,科学务实;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在人生价值观层面上,被概括为:听从祖国召唤,艰苦奋斗创业;不计个人名利,乐于帮助他人。虞师傅的一生所践行的就是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对他一生的最好写照。当我写完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欧阳梦群师弟发来一则短信:“年7月27日。师兄,师傅他走了。”在我的思绪中,那个背着地质包,骑着黑白花马的“勘察队”仿佛从天峻烟雨迷茫的大山深处走来,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我愿意愚蠢、冒昧地以一个曾经是虞叔和徒弟的身份,怀着对阴阳相隔的恩师及难以释然的父亲般的怀念和敬意,为他长歌当哭!
转载自《莽昆仑》杂志
作者简介
三木才,又名桑丹才让,天峻县快尔玛乡人,系青海省作家协会理事、青海省地方志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历任海西州档案局副局长兼海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总编、中共海西州委政研室主任、海西州文联主席等职。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独立编纂完成《海西州资源志》,90万字、《海西旅游指南》,10万字。编纂、审稿13部海西地方志书,万字,其中个人撰写万字。著有短篇小说集《漂泊的部落》、抒情诗集《心跳,珠穆朗玛》、长篇小说《失踪的康巴骑士》、长篇纪实文学《西藏·时空中布满故事》等。
----------主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点:海西州德令哈市乌兰东路20号
总监制:斯琴夫
监制:李占国、李晨
编辑:李春莲、吴海燕、阿如汗、贵青秀、乌林花、李晶、严煜坤(排名不分先后)
联系—
投稿信箱:
qq.